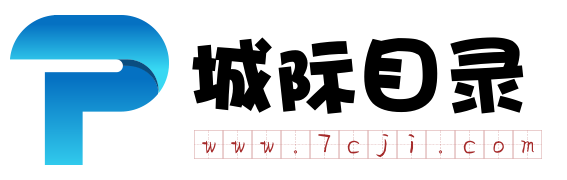托尔斯泰:一次永远的出走
一
无论是作为文学家,还是一位个体之人,列夫.托尔斯泰伯爵都堪称伟大人物。文学成就上与之齐名并同样受之无愧的,前有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是他的同胞陀思妥耶夫斯基。妥氏年长他十岁,二人生前交集不多,仅只四十岁前见过几面而已。在十九世纪庞大的世界文学谱系中,以描绘现实刻画心灵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他们俩鹤立鸡群,无可匹比,是那个璀璨而浩瀚的文学天空中最明亮的双子星座。
我的心目中,几乎每一位文学大家对现实都充满角度不同的关注,质疑和批判,但又不仅限于此。他们涵盖的范围和指向要远远超过那个界域。托尔斯泰的作品并非仅仅站在某个社会制度层面或潮流形态基础上完成的,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件薄薄的外衣而已;而是站在人性和哲学,甚或宗教的视角来展开和推进。与那些伟大前辈们一样,他是给人类的文明广厦构筑框架和添砖加瓦之人。这种人每个世代仅只一二而已。
二
为他写传的那些苏联人,尤其是文学评论家,当他们忘记了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著名语录时,书写就自如流畅起来。政治家往往力图在文艺家身上榨出更多对他们的国家治理或自身有利的东西,要求他们与自己的喜好近乎一致,彻底完美。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背离了文艺的根本,但仍固执不断地干下去……这并非不可思议:直至满足了他们的欲望或目标——梦的达成。
总有为数众多的文艺家围着他们的指挥棒旋转,甚至不惜成为帮闲以至于打手。这既源于恐惧,也源于自身的私欲。他们总是不忘在一本小说中奢求所谓的解决办法,那种经过政治的,意识形态过滤的解决之道,甚至以人民的名义,力图把文学作品变成一种应时的,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和把手。
而一个作家是不应该轻易说出人民这个字眼的,谁能代表人民呢?人民是声称人民和代表人民的那些人所能替代的吗?这个字眼被专制制度的吹鼓手们说出,被那些沙皇们说出,甚至被身处其中众口划一的人们说出,即便是大声说出,依旧令人面含羞涩,心生悲凉。望着皇帝们远去的巨大背影,夕阳之下,那群太监只能在皇宫外抚今追昔而已。
三
托尔斯泰心智的成熟在他最初的创作中就充沛地流溢着,显示出思想的独特和复杂。从一开始,他就保留了一种内省的,刺向自己的目光,一种创建“自己的宗教” 的萌芽和冲动。那种动力的核心是“爱”。抛开他的“说教”文章不论,在艺术上,人道力量,丰富而深刻的诗意,强烈的心理分析过程,道德感和伦理热情,心灵的独特体验,始终贯穿并体现在他大量的小说中。
任何一个时代,革命都是激动人心的,尤其在年轻人的土壤中激扬澎湃,这是人类社会的激情性质所决定的。当你对这个词产生了反感,便是堕入保守中去了。步入老年之后,若仍能以质疑或分析的目光来审视革命,那说明你尚未无可救药,心灵中还有令你壮怀激烈的因子,在漫长的岁月磨砺中,它们并未死灭。
在两种极端对立的争执中,差不多总是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又几乎总是少数人的专利。他们常常被认为是第三者,两面不讨好,但特立独行的人往往走的就是这条路。而那些左翼和右翼作家们,经常用文学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道德,从而完成对文学的强奸和僭越。这种僭越本质上是勉强的,背离的,也是无耻的。能从那个圈子里超脱出来无疑是一种拯救。
四
专制国家确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碾压似的文艺理论和自己的批评家,十九世纪的俄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托尔斯泰反抗着这种僭越,因为它冒犯了文学的尊严以及作为一个人自身的尊严。此外,他还生理性的讨厌那些文学纲领和写作公式,那些身裹盔甲和硬壳来写作的人们。
“没有任何一种艺术的激流能够使人规避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作家当然有自己的判断和取舍,但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判断取代不了道德的,伦理的,风俗上的,人性上的判断。一位作家最为恰切的传记就是他的作品。他的呼吸,气质,精神模样都包含其中。在古往今来的任何文艺作品中,艺术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为艺术而艺术则是愚蠢的,那是抱着自己的木乃伊在僵硬地舞蹈。
尽管每个人的语言都无法不受到制度和时代那高度概念化的,硬壳般难以楔入的陈词滥调的影响,但必须像春天的蛇一样褪去它的老皮。别让主义之类的东西搅拌到你的诗歌和小说里去,甚至别让它渗透到你的评论随笔文字中去。只有不断异化着的人才依靠它们来凑数。不要看别人的眼色和口味行事,忠实于自己的目光,感觉和判断。力求那种“深刻与锋芒的罕见的统一。”
五
托尔斯泰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从来是有所保留的,更不要说那个庞大的贵族人群了。你可能在他的书中找到幼稚、愚蠢、甚至怪异之处,但你找不到虚伪和装腔作势,找不到那些哗众取宠的东西。他的理想是所有的人们,无论原先属于哪个阶层,都能彻底而理想地平民化,成为与自然法则完全吻合的,体现最高道德理想的农民。他的很多想法都那么质朴,仿佛来自纯真无伪的原野和土地。而某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批评家们,则往往将他的这种理想贬抑为宗法制的农民立场。
他向来平视他的小说人物,既不拔高又很少缩小。你之所以有时对他的小说人物有仰视感,那是由于作者的身材和目光要比旁人高大而深远。随着暮年的临近,他希望他那些著名的主人公们能脱离各自悲剧的结局,而进入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经过沉重的求索之后进入一个阔达的境界。而在早年,他是深为那些人物的牺牲击节称叹的。这并不矛盾,安德烈公爵因生命的终结而中断的探求,在彼埃尔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在《战争与和平》中,他认为农民和士兵的作用在卫国战争中是决定性的,超过了沙皇的伟大统帅库图佐夫。他离开了自己所属阶级的立场,进入了广漠大地的低处。他的历史观向来不乏矛盾,尽管这种背离极为痛苦和纠结,却使他获得了土地和上帝带来的那种力量,也使这部书的厚度和分量更为博大,成为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巨著之一。
六
完全正确的作家恐怕多是平面的。正确常常意味着乏味。政治正确未必能使作家的书或人物“正确”。政治,意识形态,制度与宗教相比是差了几个层级的安排,但常常把它那只脏手伸到宗教的祠堂里比比划划,说三道四,甚至粗暴的把宗教降低到它们的基座下面去。
加拉塔耶夫尽管着墨不多,却无疑是他最心爱的人物之一,是他内心深处的灵光闪烁。那几乎就是他的哲学标签:不以暴力抗恶----其中有着怎样的崇高和悲悯!那种更为冷漠,更为广博也更为粗犷的命运感,那种宿命般的存在。顺从它需要更为古老的智慧,更为明晰的闪躲腾挪以及无为而治,才能获得最后的安妥。
“《战争与和平》是史诗,历史小说,风习素描,编年史,哲理文字合成在一起的新类型。”如若你由衷地为某些作家规划中的作品最终未能问世感到遗憾,恰好证明你确实成为了他的粉丝。托尔斯泰便是让许多人感到可惜的这样一位作家,他有至少两至三部长篇作品被中途放弃了。无论这些作品是历史小说还是社会小说,它的缺席带来的巨大遗憾莫不如此。
他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天然反对者,是自由主义的诘难者,是农奴制罪恶的控诉和谴责者,是沙皇统治的批判者,他有一套基于爱和土地以及农民的自己的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方法论。他的作品是以爱---而不是对自己的爱---为基础的,是以从不间断的探求,挫折,怀疑和动摇,悔恨和自责来加以描绘的。他不是自私而简单的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但始终有一条彩虹若隐若现地悬挂在他的雨中或是雨后的天外,这就是遥远的人类之爱。
受传统的的某种审美影响,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了“模型”的意义,这多少损害了活生生的“人”,这难道不也是存在于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异化吗?人要比模型更有意味,那种活生生的,原创的意味。模型是批评家更感兴趣的东西,他们的声誉往往是通过模型建立起来的,他们把作品中的人与他们自己一道变成了木偶。
七
《安娜。卡列尼娜》的多重意味之一在于,安娜并非一个荡妇,但却卧轨而去。即便与情夫在国外生活的日子里,她仍无法获得宁静的幸福,她获得的只是“不可原谅和不被祝福的幸福”。她渴望过上“新人”的生活,却做不了新人。安娜之死实为作者的意在控诉。只有精神上的丰富与感情上的禀赋彼此相当的人才可能维系较为长久和谐的夫妻生活。这本书的另一个非凡之处是,让当时各种流派的批评家们沿着各自的河道见仁见智,争吵不休。
除了“崇高的感情上的宗教”,“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之外,托尔斯泰的力量还在于不仅不否认,而且赞颂尘世生活。他是有史以来在历史与现实的激情交汇中与自我融合的最好的巨匠。艺术感觉与他同样好的还有他的同时代人屠格涅夫,只是后者的格局要小得多。在人性的深入剖析上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是他唯一的对手,在这条路上,后者似乎比他走的更远,也更为崎岖。
托尔斯泰后三十年的主要追求是“拯救灵魂”,首先是自己的,然后是别人的。《复活》表面看去似乎像是一部忏悔他青壮年时期的“伪自传”, 但绝不仅限于此,它直接触及到堕落甚或罪恶的灵魂怎样“复活”这一古老的命题。年逾古稀的托尔斯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跋涉之路,在自己的笔下人物玛斯洛娃和聂赫留道夫身上最终完成了道德的复活。那是他灵魂的复活,也是人世间巨大的精神的复活。他携带着他众多的人物攀登着命运的最后那几道台阶。
而这种攀登尽管有迷途,停顿,悲观和挫折,但也有喜悦,顿悟,满足和自圆其说。孤独者怎能拒绝自圆其说?因为世界的嘴脸过于严酷。“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就要“放弃一切生活中的娱乐,必须劳动,驯服,忍耐和慈悲为怀。”他把这种拯救寄予到了日常生活中,由一种仪式,演化成常年如一日的日用起居。这也造成了他与家庭的某种悲剧。这种巨大的矛盾导致了他82岁那年死于途中的最后出走。那次出走也是他推迟了数次之后的唯一的出走:一次永远的出走。
这是受难,更是飞升。
作者:阿末
- 上一篇: 一路奔跑,追逐梦想
- 下一篇: 落一束夏,又落两场冬